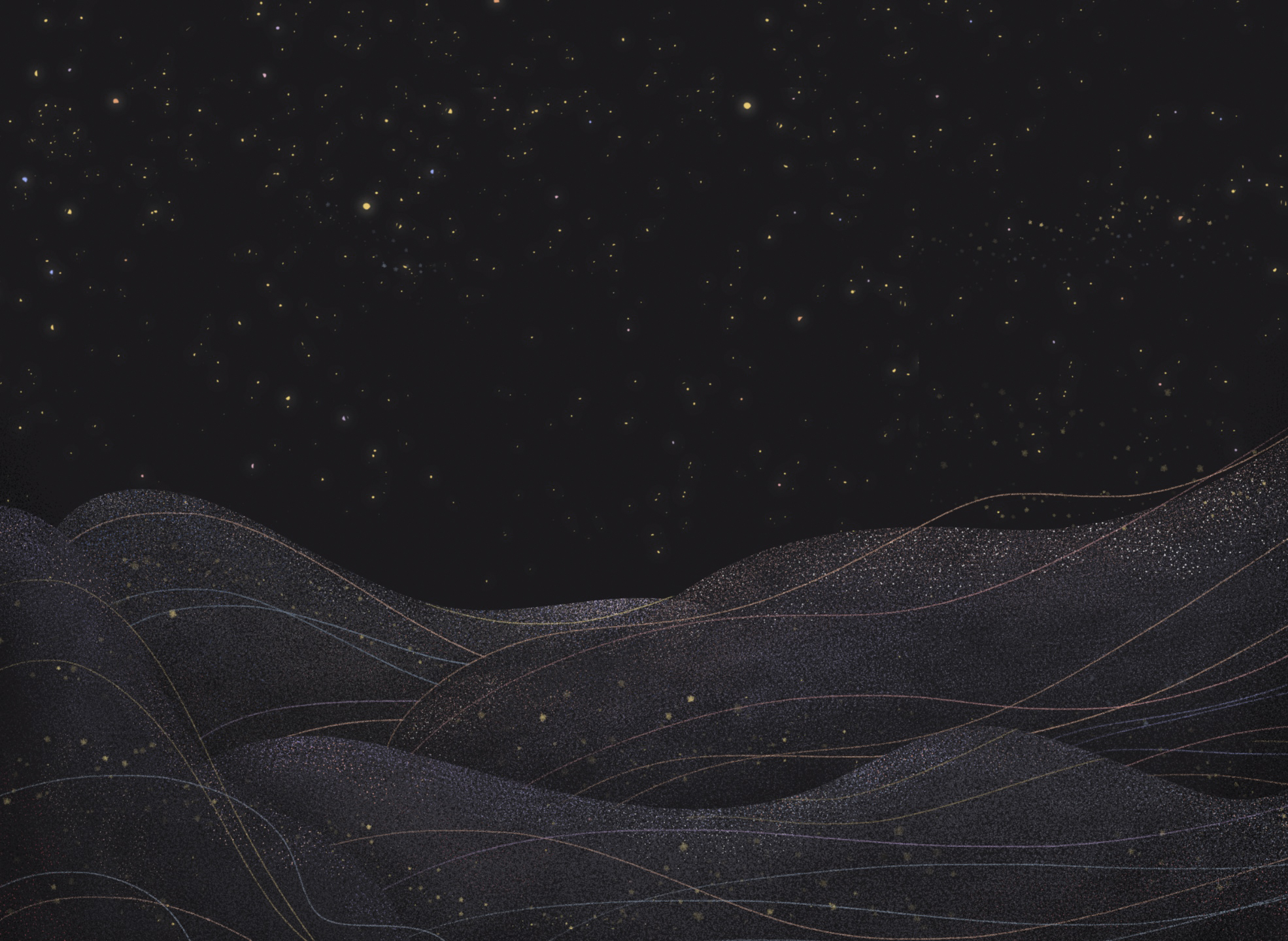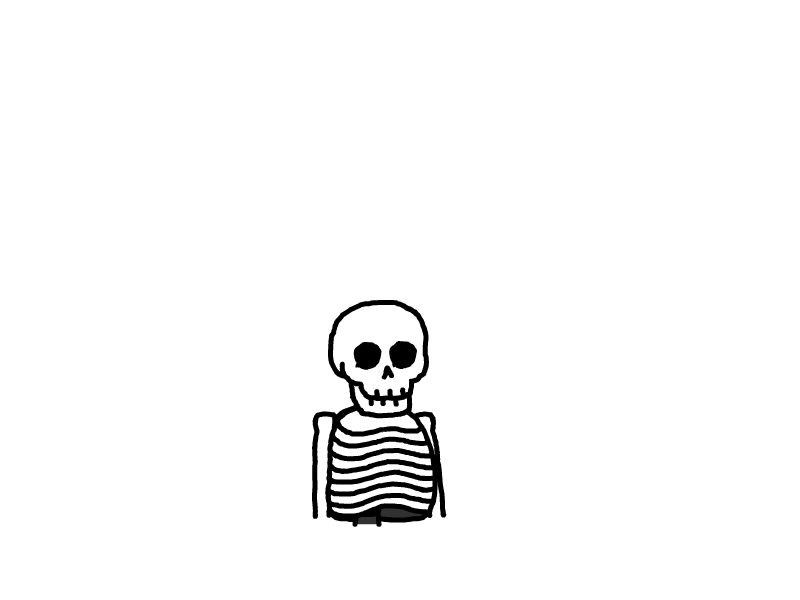老张死了,热死的
老张之死
校门口铁皮屋子里的老张死了,热死的。
我向来知道那屋子窄小,只容得下一床一灶,窗是钉死的。三架电风扇嗡嗡地转,却只揽得热气打着旋,猫毛在热风里沉浮。大爷养了七八只野猫,电扇原是给猫预备的。猫们此刻围着空碗打转,碗底干得发亮,像几只空洞的眼睛。
老张蜷在铺板上,身子薄得像片枯叶。床下塞着双新棉鞋,标签还未撕去,蓝布棉袄搭在椅背——皆是毕业生弃在楼道,他喜滋滋拾回的。“留着过冬哩。”他说。冬是有的,人却没了。
胃里有些翻搅。我记起上月见他煮挂面,白水翻滚着,蒸汽蒙住那扇打不开的窗。“食堂贵哩,”他擦起衣襟揩汗,“面条顶饱。”面汤里浮着几点油星,猫在脚边喵喵地叫。一只三花猫右眼糊满脓,他总念叨:“得空带它瞧大夫去“ 。空其实是有的,没有的是钱——校里欠了他八个月工钱。
手机震了。是校长在毕业典礼上的讲演,彩绸在空调冷风里飘拂,讲的是“仁爱精神”。前些日去行政楼交材料,门缝里溢出的寒气,蛇一样咬人的脚踝。

本文为原创文章,完整转载请注明来自 BoJack'Blog。欢迎转载,让声音传播的更远。
评论
匿名评论
隐私政策
你无需删除空行,直接评论以获取最佳展示效果